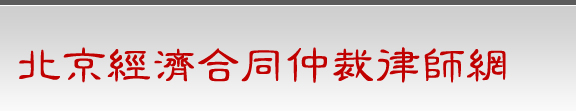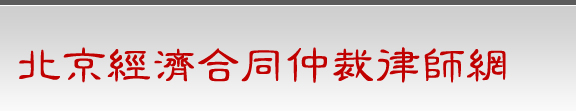|
实务分享
|
|
 |
| 合同债权与仲裁条款转让的再审视——基于实体法、程序法和冲突法的视角 |
|
合同债权与仲裁条款转让的再审视——基于实体法、程序法和冲突法的视角
【内容提要】合同转让时,尤其是合同权利转让时仲裁条款是否随之转让的问题,是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目前,国内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以及司法实践支持仲裁条款自动转让。但仲裁条款自动转让的理论依据并不充分,也未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对于仲裁条款转让的论证仅仅限于国内法上的视角,并未考虑国际合同转让中仲裁条款的效力和相关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等问题。本文旨在从实体法、程序法和冲突法的多维角度,进一步探讨合同仲裁条款转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对当前国内外的立法与实践进行评判,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国内的法制和实践。
【关键词】合同债权 仲裁条款 债权让与
[Abstract]Whether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a contract follows the assignment of contractual rights to the assignee has been one of important ques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transfer is adopted in the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it is not theoretically persuasive and has not resolved the related problems. Moreover,the discussion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arbitration clause is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law,however its trans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is ignored. This article is to further discuss the related issues concerning the arbitration clau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bstantive law,procedural law and conflict laws,and make a brief comment on the domestic law and practice,aiming at improving the present domestic legislation.
[Key words]contractual rights;arbitration clause;assignment of debt
一、问题的提出:仲裁条款随合同自动转让?
合同转让的实质乃合同主体的变更。按其转让内容,可分为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合同义务的转让以及合同权利的转让三种情形。[1](p411)理论界将其归纳为合同承受、债务承担和债权让与三种情形。根据各国的立法和实践,在合同转让情境下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转让的问题上,主要有自动转让和非自动转让两种立场。
所谓仲裁条款自动转让(Automatic Assignment Rule),是指合同转让时,只要受让人没有作出对仲裁条款拒绝的意思表示,仲裁条款随合同其他条款一并转让,受让人应受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2](p65)根据国内学者代表性的观点,合同转让之于仲裁条款的效力,主要是针对债权让与时仲裁条款是否随之转让的情况。[3](p32)因为在合同承受和债务承担时,多经合同相对方和受让方同意,适用自动转让规则在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不存在大的争议。[4](p162—163)但债权让与时往往未经合同相对方(债务人)同意,仲裁条款对受让人和债务人的效力受到了质疑。所以,仲裁条款是否随合同转移的问题,主要是债权让与时仲裁条款是否自动转移的问题。
对此,国内学者多支持仲裁条款的自动转让。其依据主要包括:附属权利说,仲裁条款是主合同之组成部分,应该与合同其他权利条款一并转移;[5](p49)利益期待说,仲裁条款自动转移保护了让与人和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和将争议交付仲裁的合理期待;[6](p220)协议解释说,仲裁条款是否随合同转让,是转让协议的解释问题,解释要服从当事人希望通过仲裁解决纠纷的意愿;[4](p163)程序保障说,仲裁条款自动转移原则是保证仲裁程序顺利进行的不可或缺的原则。[6](p221)
然而,反对仲裁条款自动转让者则认为:合意是仲裁条款生效的根本,仅仅通知债务人而不是取得债务人同意的,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并未形成合意;仲裁条款的确定以及仲裁机构的选定,出于当事人的特定立场、背景和身份性利益;仲裁条款具有独立性,合同转让仅是指实体权利义务的转移,并不必然涉及仲裁条款的转让;仲裁权利是程序上的权利,不受支配合同实体权利的规则的约束。[7](p139)总之,“不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全部转让还是部分转让,除非有关当事人明示接受原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否则,原合同仲裁条款不能约束转让后的当事人”。[8](p232)
毋庸置疑,仲裁制度的核心是仲裁协议,不论是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形式还是单独的仲裁协议形式出现。尽管国际上一直有“仲裁自治体制”和“罢黜国家法律”的主张,[9](p85)但这种论调过分强调了当事人意思自治而忽略了意思自治仍需依存外部法律制度这一现实,追随者并不多。所以,在衡量当事人“合意”这一问题上,一方面仲裁协议仍是仲裁庭凭以成立的唯一依据;另一方面,现实世界中仍需要包括《纽约公约》、国内法、甚至“示范法”等一系列的规则对仲裁协议进行规制。[10](p7)一来确认该等仲裁协议是否存在,二来对当事人的意思进行确定以充分实现其提交仲裁的意愿。
所以,考察合同权利让与情形下的仲裁条款的转让效力问题,取决于对相关当事方主观上“仲裁合意”的形成以及外部法律因素对“仲裁合意”的干预。
二、合同债权转让中影响仲裁合意的特殊问题
(一)受让人同意仲裁
在合同权利转让时支持仲裁条款自动转让的观点中,多“推定受让人同意接受仲裁”的主张。因为受让人有足够的理由获得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的信息,如不愿将与基础合同中另一方的纠纷交付仲裁,则应在与转让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明确拒绝接受仲裁条款。但近期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尽管支持仲裁条款转让,却未见“推定同意”的结论。
纽约上诉法院早在1924年的一起案中⑴,依据“任何一方不能剥夺对方基于仲裁条款应获得的权利”为由认定受让人须遵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在1983年纽约南区法院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 Bas v.Amoco Oil Company一案中⑵,法院认为仲裁条款如不自动转让,原合同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将会被其他方式所替代,而原合同的权利在转让中将会被单方篡改。其后,在1992年俄亥俄南部地区法院Roben Lamb Hart Planners and Architects v.Evergreen Ltd.一案⑶,以及2000年佛罗里达州第一巡回上诉法院Cone Constructors Inc.V.Drummond Community Bank一案⑷,均以“维持权利平衡”这一规则确定仲裁条款转让后的效力。
换言之,上述司法判例支持仲裁条款转让实则出于权利的“稳定性”,而非必然推知受让人与原合同债务人之仲裁合意。对此,法国最高法院和巴黎地方法院的两起案件中也接受了这一立场:在合同的债务人援引仲裁条款抗辩时,之所以驳回受让人的诉讼请求,其目的在于使仲裁条款的效力并不因转让而受到影响,避免合同的转让使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得到不同的法律程序的处理⑸。与此同时,权利“稳定性”这一方法论在菲律宾最高法院⑹、美国纽约南区法院⑺、以及其他地区法院的判决中也得以广泛认同⑻。在国际仲裁界,国际商会仲裁院在ICC No.3281(1981)一案中则援引了“合理原则”(Principle of reasonableness),认为仲裁条款系以执行原合同衍生权利之措施,且自动转让有利于保护原合同债务人之利益,使债务人免于被迫接受国家法院的管辖和对其不利的诉讼程序。[11](p4)这与“维持权利平衡”或“稳定性”的裁判方法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可见,支持受让人遵守合同仲裁条款的,非因“受让人有机会审视合同全部条款”而推定其同意。毕竟在权利转让的实务中,受让人多关注合同的实体权利内容,如果没有专门提示,受让人未必有理由充分知悉仲裁条款,且合同转让并不必然导致在原文本上签字,而是通过另外的转让协议进行。因此,没有相反约定便推定受让人知悉并同意仲裁条款,只不过是出于支持仲裁或便于实际解决问题而预设的一种立场而已,它本身并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理基础。
正因如此,另有诸多国家和地区以受让人与原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未形成合意为由,认为权利转让并不发生仲裁转让效果。例如,英国法院在1928年的Cottage Club Estates.v.Woodiside Estates Co.一案中,认定合同转让并不涉及仲裁条款转让,因仲裁条款本质是特定个体之间的约定,只约束签署合同的当事人。而根据美国纽约州的地方法律,如果没有受让人和另一方当事人明确的同意,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并不必然在他们之间具有约束力。在1992年Zimmer v.Cremascoli一案中,意大利最高法院也认为,根据《纽约公约》,转让本身不足以证明受让人对仲裁条款的自动接受,仲裁条款的转让需符合“可证明、明确而不含糊”这一条件。[12](p131)
(二)仲裁条款的身份属性之于仲裁合意
在判断合同相对方的主观状态乃至仲裁当事人的合意时,另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仲裁条款是否具有身份性因素。有代表性观点认为,当今商事合同中订入仲裁条款已非常普遍,“再说其属人特性显然已不合时宜”。[13](p85)但是,仅仅从仲裁成为普遍性纠纷解决方式这一现象而否认仲裁条款的“身份性”因素,依据显然不充分。仲裁程序有别于诉讼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非公开性,基于非公开性而选择仲裁,除了商业因素外,不排除对合同当事人身份性因素的考虑。作为纠纷解决的替代方式,选择仲裁更有助于自主地确定利益关系的实现模式,当事人选择仲裁时无疑会考虑双方的交互性身份关系。毕竟选择仲裁是一个方面,而选择与谁仲裁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合同的相对方之间同意仲裁,未必意味着同意与第三人之间仍然适用仲裁。
正因如此,合同债权转让过程中,阻止受让人与原合同相对人形成合意的身份性因素,又被称为“默示性”因素。之所以称之为“默示性”,是因为它们初衷不在于阻止仲裁条款转让,但他们服从于合同其他特定目的,或者基于理论上的仲裁独立性特征而阻止了这种转让。[11](p6)如果合同是出于特殊资格、能力、保密性或长期合作关系等“特殊原因”而订立,该合同便具有了“默示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潜在的受让人或者替代转让方的其他机构或个人,在合同的履行上将无论如何也不能替代原当事人。
在1997年EMJA上诉案中,EMJA便主张仲裁协议的订立往往是当事人之间人身信任关系的结果,而债务人与受让人不存在这种关系,不应受原仲裁条款的约束。瑞典最高法院对此虽认为“在商业实践中基于人身信任关系才订立仲裁条款极为罕见”,但亦未完全否认基于信赖、保密或特殊关系下合同仲裁条款的特殊性。在Application of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V.Harrions&Crosfield,Ltd.一案中⑼,美国纽约南区法院认为“合同不要求对方当事人特殊技能或者不做特殊保密关系安排的”,合同的仲裁条款可以转让。这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当事人特殊保密安排下的合同仲裁条款不能自动转让。有时,合同的“身份性”因素不是影响仲裁条款转让的“决定因素”,而“决定因素”的认定也没有确定的标准。[14](p431)所以没有通用的标准来确定仲裁条款是否具有身份性质,而且这样的标准也没有必要存在。基于此,在Cottage Club Estates v.Woodsides Estates Co.一案中⑽,英格兰上诉法院认定仲裁条款基于个案,可以具有“身份性”,但在其后的Shayler v.Woolf一案中⑾,英格兰上诉法院则认为仲裁条款不具有身份属性。所以,尽管理论上,“仲裁协议的形成并不主要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保密关系,而是在于仲裁的优势”。[11](p6)但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并没有否定仲裁协议的“属人”特性。所以,客观的做法应当是,即使在单纯的债权让与的情况下,“应强调债权转让应通知对方当事人,并且在对方当事人未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仲裁条款的效力”。[6](p227)
(三)仲裁条款义务属性对仲裁合意的影响
仲裁条款能否随合同自动转让的分歧,还在于仲裁条款本身的属性。合同的附随权利连同基础性权利自动转让,已是国内法上的普遍做法⑿。但是,诸如国内民商事法中规定的衍生权利与基础权利的附随关系,未必契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即仲裁条款是否属于“权利”的范畴,这仍然是一个待决问题。例如,在法国的仲裁司法实践中,以及纽约州的法律,则认为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主要是义务属性而非权利,因此需要受让人的明确同意方可产生转让的效果。[15](p151)英国在1997年的Tito and Others v Waddell and Others这一代表性案例中也确认,合同中的权利内容可以转让,但是义务性内容仍由转让人承担⒀。本案中,英国司法认为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并不随合同转移,因为仲裁条款为受让人设定了义务,而第三人不受制于他人合同所设定的义务。
在瑞典EMJA一案中⒁,针对原审法院支持仲裁转让的决定,受让人EMJA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法院认为,受让人在转让中不能取得比转让人更优的地位,这项原则对仲裁条款同样有效。这实际上是将合同中的仲裁赋予了义务属性,至少对合同受让人来说,必须通过原定的仲裁条款解决纠纷是其义务,而不得出于自己的便利或利益废弃仲裁而选择诉讼。
如果要求受让人遵循仲裁条款设定的义务的话,那仲裁条款对转让人来说亦为义务范畴。如此一来,合同实体权利的转让并不意味着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亦为“权利”而自动转让。认为合同权利转让无需相对方同意,进而认定仲裁条款转让无需原合同相对方或受让人同意的观点,实际是忽略了仲裁条款的义务属性。
在合同相对方的主观意愿上,还有观点认为,合同债务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合同债权有可能会转让给不特定的人,如果不同意仲裁条款随同转移,“就拥有在订立合同时作出明确表示的权利,否则应视为其同意”。[16](p115)然而,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相对方和彼此选择的交易对象,任何一方当事人首先期望由对方而不是其他人来履行合同,合同的转让恰恰是例外情形。当然,有些情况下,合同仲裁条款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在仲裁程序启动时并不明朗,只有在仲裁裁决作出时才可以确定。[10](p9)但进一步讲,即使不能完全肯定仲裁条款的义务属性,那么仲裁条款包含权利与义务双重属性的论断则是最客观的。因为仲裁条款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合同。而现实中合同的权利与义务总是相生相伴。[17](p996)仲裁执行中对一方的权利,对另一方来说就是义务。因此,作为义务属性,它不能自动转让给受让人或其他第三人。尽管有学者主张这种观点不能成立,但现实也有许多判例支持这种做法⒂。
如此一来,仲裁条款的转让不仅仅是受让人明确同意的问题,恐怕还需原合同相对一方的同意。而仲裁条款自动转移理论对此并未确证当事人之仲裁合意,这恐怕也是其无法克服的缺陷。
三、仲裁条款的实体性与程序性解释方法
在讨论合同仲裁条款的权利或义务属性对仲裁条款转让的影响时,还有一个上位问题:即合同转让的仲裁权利或义务是实体性还是程序性的问题。
对此,仲裁条款的独立性理论指出了仲裁条款独立于合同实体内容。然而,对仲裁条款的独立性之于仲裁条款的转让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解读并不一致。一个基本的观点认为,独立性首先在于仲裁的约定不能转让给受让人,因为当事人转让的合同权利为实体权利,根据程序与实体区分的理论,仲裁条款并未发生转让。或者说,“受让人所受让的权利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合同权利,而是法律规定的二次权利或救济权,所以,自然不能得出仲裁条款随合同转让而自动转让的结论”。[18]然而,相反的观点认为,仲裁条款的自治应解释为受让人应受制于仲裁,例如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协议,同样适用于仲裁。因为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旨在任何情况下鼓励和保证仲裁的执行。[19](p9—10)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以及美国地方法院的判例也认同这一观点⒃。
尽管对仲裁独立性理论做出不一致的解读,但可以肯定的是,独立性理论并非仅仅是出于“支持仲裁”这一实用性目的所支撑的⒄。因为“支持仲裁”仅仅是一种实用取向而非理论建树。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本质上于它是解决实体纷争的程序性救济机制。程序事项独立于实体问题,否则,仲裁条款则无法实现救济性职能,实体权利的保障也成为一句空话。诚然,仲裁条款的独立性要求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通过仲裁解决纠纷,但原合同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是否受仲裁条款约束的问题,就不是仲裁条款的独立性这一原则本身所能解决的。
在支持仲裁条款转让的实践中,英美法系多从仲裁条款的程序性入手,在前述纽约地方法院在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 v.Amoco Oil Company一案中认为:受让人受制于合同原当事人之间商定的“救济措施”⒅。在法院看来,仲裁条款无疑是一项程序性措施。相反,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多地从合同实体性利益方面作为切入点。例如,法国最高法院在2000年Banque Worms v.Bellot一案中则认为:“国际仲裁条款,其效力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随同债权有关的权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转让的方式和效果等同于原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效果。”⒆在这里,法院强调的是合同实体法上的效果。与之相似,巴黎上诉法院在C.C.C.v.Filmkunst一案中认为,转让方向受让人转移的虽然是纠纷解决方式,但受让方须受制于仲裁条款的约束,因为这事关合同中约定的金融权益,受让人与合同债务人对于提交仲裁都存在着金融利益⒇。显然,法院在该案中认定仲裁条款与合同实体利益已无法分割。
仲裁条款与实体权利内容如此紧密,以至于在欧洲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的实体法中涉及了仲裁条款的转让事项。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一系列判决认为,《德国民法典》第401条之规定,旨在强调仲裁条款类似于合同的担保,是付款得以执行的保证,因此,仲裁条款随合同自动转让(21)。同样,《奥利地民法典》第1394条在合同权利转让中也暗含着“受让人受让的合同权利同于转让人的权利”,这意味着仲裁条款自动转让的效果在奥地利得到认可。另外,《瑞士债务法》第170(1)条规定,“合同债权的转让时,与债权有关的好处和债权衍生的权利一并转让”。尽管根据法国的仲裁法,仲裁条款属于程序内容,并将其视为义务负担,但《法国民法典》第1692条强调了“债权转让包括与债权相关的附随权利一并转让”。
四、仲裁条款转让中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在合同权利和仲裁条款的转让中,至少存在着合同的转让与受让、仲裁条款的转让与受让、合同的受让人与原合同相对人之间以及仲裁条款的受让人与原仲裁条款相对人之间四组法律关系。而且在现实中,针对合同权利的转移,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转让协议——无论是以书面还是口头形式。转让协议本身亦有其相应的法律适用规范和准据法。可以肯定的是,转让协议的准据法可以通过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意思自治或最密切联系原则来实现,但对于转让协议的标的,本质上属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因此还需借助原合同的准据法予以确定。所以,对于转让协议是否成立、有效以及可执行等问题,需要重叠适用转让协议自身的准据法和原合同的准据法共同确定。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基于赌博合同关系创立,根据其准据法有效并可转让。但当该等权利跨国转让给第三人时,该转让协议是否成立、有效的问题,原合同的准据法就无法替代转让协议的准据法。所以,国际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客观上需要两个以上的冲突规范指引的准据法才得以最终确定(22)。
参照合同实体权利义务的转让,仲裁条款转让的标的是仲裁权利和义务,因此对于仲裁权利义务内容的确定,仍要借助仲裁条款的准据法来确定。但正如合同的准据法不能解决合同转让的全部问题那样,仲裁条款的准据法也不能调整仲裁转让的全部内容。因为即使根据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允许自动转让,对于第三国的受让人来说未必适用。因此,仲裁条款转让还受制于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准据法。但实践中转让协议往往没有提及仲裁条款,当然也无法就仲裁条款转让约定准据法,此时,仲裁条款的转让效果面临如下法律选择:第一,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仲裁转让的准据法;第二,适用仲裁条款的准据法;第三,适用转让协议的准据法;第四,直接适用纠纷解决地的程序法来决定转让的效果。
此时,识别制度将发挥作用。正如前述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做法那样,如果将仲裁条款的转让视为合同转让的附属内容,则需要根据转让协议的准据法一并确定仲裁转让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仲裁条款较之原合同独立适用法律,因此仲裁条款转让可以,适用转让协议的准据法,但非原合同的准据法。总之,第三种法律选择是可行的。
如果将仲裁的转让识别为程序问题,则直接根据纠纷处理国家的仲裁法来确定仲裁转让的效果。例如,订有仲裁条款的合同在发生国际转让时,若受让人针对原合同的债务人直接在本国提起诉讼或仲裁的,那么法院或仲裁机构首先审查是否约定了仲裁条款的转让以及法律适用问题,如果没有,则受案法院可根据当地法律,将仲裁条款转让识别为程序问题,直接适用本国的仲裁法上规定,或者由仲裁机构根据其仲裁规则确定仲裁条款是否得以转让。
对于第二种法律选择,是否可以直接根据原仲裁条款的准据法来决定受让人与原合同债务人之间的仲裁法律关系?参照合同权利转让的法律适用规律,仲裁条款转让的法律适用与原合同仲裁条款的准据法之间不可割裂,但直接适用仲裁条款的准据法无异否定了仲裁转让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客观存在。除于非纠纷处理地国家的冲突法规定仲裁条款的转让适用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否则,仲裁条款转让的法律适用与原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法律适用是两个相关联但却不同范畴的问题。因为影响仲裁条款转让效果包括了转让人与受让人、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仲裁法律关系,原仲裁条款相对人之间确立的仲裁条款的准据法未必契合仲裁条款转让后的法律关系的准据法,仲裁条款原当事人之间选择的法律,也非受让人与转让人(或债务人)之间选择的法律,因为他们之间“合意”尚存争议,谈不上共同选择法律的问题。
所以,解决仲裁条款转让需要单独的法律适用规范,最好的办法是转让人与受让人约定仲裁转让的法律适用,如果没有这种约定,则考虑适用与仲裁转让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在决定仲裁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执行问题上,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应得到合并适用。但是,如果将仲裁转让视作程序法事项的,可直接适用程序法上的规定来决定仲裁条款是否转让。而如果将其视为实体权利义务附属内容的,可适用合同权利转让的准据法,或者直接适用实体争议的准据法来决定仲裁条款是否有效转让。例如,国际商会仲裁院于1977年审理的第1704号案件裁决,直接根据解决争议所适用的法国的实体法,裁决受让人受原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支配。在1977年的第2626号案件中,仲裁庭认为根据德国实体法,受让人应受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23)。然而,在1991年的Fraser v Compagnie Europeenne des Petroles一案中,仲裁庭认为仲裁条款受合同相对性原则约束,因此无法适用于转让协议,除非当事人另有明确约定其适用(24)。
需要说明的是,探讨仲裁条款是否自动转让以及仲裁条款转让的法律适用问题,主要是解决仲裁合意是否形成的问题。考虑到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还包括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仲裁协议的形式、仲裁协议内容的合法性以及可仲裁性等问题,尤其考虑到上述问题需“分割”适用法律的现状,仲裁条款的转让事项就更需专门的法律适用规范来调整了。
五、我国内地的立法和实践
在我国内地,200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之前,司法实务中就已经通过个案形式认可了仲裁条款对合同受让人的约束力(25)。2006年《〈仲裁法〉司法解释》的实施,为合同受让人受仲裁协议条款约束确立了裁判上的依据。根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9条,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
上述规定吸收了仲裁条款自动转让理论,但也仅仅是在我国内地解决了仲裁条款转让的理论争议,是否适用于涉外仲裁条款的转让,尚不明确。与之相关的,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8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或者仲裁地法律。”应该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18条的规定,根据国际上普遍遵循的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原则,对于涉外仲裁条款专门规定了独立的法律使用规范。但是,正如上文论述的那样,仲裁条款的法律适用规范与仲裁条款转让的法律适用规范属不同性质的问题,另需相应的立法予以解决。
当然,在立法资源无法满足现实需要的情况下,可否通过司法解释的途径,将上述仲裁条款的法律适用规定做扩展解释,适用于仲裁条款转让的法律适用范畴?但如此一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18条中“当事人”能否包括“受让人”和“原合同债务人”?毕竟,仲裁条款的法律适用规范是基于仲裁双方就仲裁达成了合意,旨在解决其效力和执行问题;而仲裁条款转让的法律适用旨在通过准据法来确定受让人与合同转让人以及债务人是否存在“仲裁合意”的问题。不过,考虑到国际上对待仲裁条款转让的实践中淡化“受让人同意”和强调“维持权利平衡”的立场,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不妨对之做扩张解释,但仅作权宜之计。
还有另一种选择,那便是在涉外仲裁的司法审判中,将仲裁条款的转让定性为程序问题,进而直接适用现行《仲裁法〈司法解释〉》,裁定受让人受原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约束。当然,从程序规制的角度,仲裁机构完全也可以在仲裁规则中采纳类似的做法,通过程序性规则的适用来实现或保证合同仲裁条款的转让效果。在这方面,在国内涉外仲裁机构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中,规定了“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转让……均不影响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效力”等类似性规定(25)。但诸如此类的规定,均基于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原则,旨在强调合同转让不影响原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合意,而非规定受让人仍遵守原合同仲裁条款。如达此目的,不妨专门予以明确,并通过对仲裁程序规则的适用,直接解决国际合同转让中仲裁条款是否转让的问题,从而也避免了繁琐的法律适用问题。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或实体法领域中统一规则的创制上应有所建树。对此,各国法院可根据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趋势,在确立“自动转让”原则及例外规则的基础上,统一的解决方案和解释规则将变得很急迫。[11](p9)这也正是当前在合同转让对仲裁条款的影响这个问题上,国际法制的提供与需求之间矛盾的现状写照。
【作者介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Hosiery Manufacturing Corp.V.Goldston 238 N.Y.22.(New York Court of Appeal 1924),p.28.
⑵Banque de Parus et des Pays—Bas v.Amoco Oil Company 573 Federal Supplement 1464(S.D.N.Y 1983).
⑶Robert Lamb Hart Planners and Architects v.Evergreen Ltd.787 F.Supp.753,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Southern District of Ohio 1992.
⑷Cone Constructors Inc.V.Drummond Community Bank 754 So.2d 779(1st District Court of Appeal of Florida,2000)
⑸Paris,(1re Ch Urg.),20 April 1988,Rev.Arb.,1988,570;Cour de Cassation,19 October 1999,Revue de l’Arbitrage(Rev.Arb.) 2000.
⑹Heirs of Augusto L. Salas,Jr v.Laperal Reality Corp.,(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lippines,13 December 1999,G.R.No.135362).
⑺除上面提及的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 v.Amoco Oil Company案件外,纽约南区法院在下列一系列案件中均采用了“维持权利平衡”、“权利稳定”等以支持仲裁条款随合同权利自动转让:Instituto Cubano v.The MV Driller(11 February 1957,148 F.Supp. 739);Lumbermens Mutual Casualty Company v.The Borden Company(7 April 1967,268 F.Supp.303);Thomson—CSF,S.A.V.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31 October 1983,573 F.Supp 1464);GMAC Commercial Credit LLC v. Spring Industries,Inc.(24 April 2001,00 Civ.2893(NRB).
⑻DiMercurio v.Sphere Drake Insurance Plc.(U.S.Court of Appeals,First Circuit,31 January 2000,202 F.3d 71).
⑼Application of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V.Harrions&Crosfield,Ltd.(106 F.Supp.358(S.D.N.Y 1952)360.
⑽Cottage Club Estates v.Woodsides Estates Co.26,(1928)2 KB 463,466.
⑾Shayler v.Woolf(1946)Ch.320(323).
⑿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692条;《荷兰民法典》第6—142条;《比利时民法典》第1692条;《瑞士债务法典》第170(1)条的规定。
⒀Tito and Others v Waddell and Others[1997]2 WLR 496(Ch.D).
⒁See Peter Dyer&Jan Sallnas,“Sweden:Arbitration and Assignment of Contract”,Int.A.L.R.1999,2(1),N2—3.也可参见赵健:《长臂的仲裁协议:论仲裁协议对未签字人的效力》,载《仲裁与法律》2000年第2期。
⒂例如Daniel Girsberger在“权利与仲裁协议的转让”一文反对仲裁条款的义务属性,参见Daniel Grisberger and Christian Hausmaninger:Assignment of Rights and Agreement to Arbitrate.1992 8(2),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p.121.但美国的许多联邦法院在判例中认为仲裁条款的人身属性,相关案例参见AT&T Technologies,Inc.V.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 et al.,475 U.S.,643.,649.,106 S.Ct.,1415,1419;Lachmar v.Trunkline LNG Company,753 Fed.Rep.2nd Series,p.8.10;Laborers Intern.Union v.Foster Wheeler Corp.,868 F.2d 573,p.576.
⒃See Trade Finance Inc.V.Bulgarian Foreign Trade Bank Ltd.(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5 May 1997);Hosiery Manufacturing Corp.V.Goldston(238 N.Y.22,New York Court of Appeal 1924).
⒄有观点认为:仲裁条款是以实用主义经验促成的,其独立性就是为了推动仲裁制度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当事人的仲裁意愿。参见李彤:《论合同转让中仲裁协议对未签字人的延伸效力》,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7期,第114页。
⒅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 v.Amoco Oil Company,31.10.1983,S.D.N.Y.573 F.Supp.1464.
⒆Banque Worms v.Bellot,Cass.le Ch.C.,05.01.1999,No.S.96—20.202,Rev.Arb.2000,85(86)
⒇C.C.C.v.Filmkunst,CA Paris,28.01.1988,1988 Rev.Arb.567.
(21)参见Bundesgerichtshof:Ⅲ Zivilrecht 2/96,2 October 1997;Bundesgerichtshof:Ⅲ Zivilrecht 18/77,28 May 1979,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Bundesgerichtshof:Ⅲ Zivilrecht 103/73,18 December 1975.转引自Andrea Vincze,Arbitration Clause—Is It Transferred to The Assignee?Nordic Journal of Commercial law,Nordic Journal of Commercial Law,Issue 2003(1).
(22)例如:欧盟2008年《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第14条规定,债权转让的合同性内容适用转让合同的准据法,而债权转让的财产性内容则适用被转让债权的准据法。
(22)See 105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J.D.I.]977(1978).参见刘晓红著:《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理与实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5页。
(23)Revne de L’Arbitrage 73,p.74.See also Alan Redfern and Martin Hun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51,(4th ed.2004).
(24)例如,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河南公司与辽宁渤海有色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纠纷上诉案(2000)经终字第48号。
(25)参见2012年《贸仲规则》第5条第(4)项的规定。
[1]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Sigvard Jaivin.Assignment of Rights Under a Contract Containing an Arbitration Clause——Assignee Bounded to Arbitrate,Decision by Sweden’s Court in the“EMJA”Case[J].Swedish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997 Yearbook of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3]赵秀文.敏感的转让一国际商事仲裁协议转让及其适用法律[J].国际贸易,2000,(12):32—35.
[4]宋连斌.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5]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刘晓红.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理与实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现代化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8]陆效龙.涉外仲裁协议的司法审查[M]//: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与研究(2001年第1卷).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9]Alan Redfern and Martin Hun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ion(5th ed)[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0]Marcia Ashong.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greements and Non—Signatories:The Challenge Going Forward for The Globalized Petroleum Industry.[2012—12—10].[EB/OL].http://www.dundee.ac.uk/cepmlp/gateway/files.php?file=cepmlp_car14_6_238166109.pdf.
[11]Andrea Vincze.Arbitration Clause—Is It Transferred to The Assignee?[J].Nordic Journal pf Commercial law,Nordic Journal of Commercial Law,Issue 2003(1).
[12]Daniel Girsberger and Christian Hausmaninger.Assignment of Rights and Agreement tp Arbitrate[J].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Vol,8,1992(2).
[13]侯登华.合同权利转让仲裁协议效力的再认识[J].法律适用,2005,(4):83—84.
[14]Emmanuel Gaillard,John Savage.Fouchard Gaillard 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M].Gaillard and Savage(ed),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9.
[15]Alan Redfern and Martin Hun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M].London,Sweet&Maxwell,4th ed,2004.
[16]李彤.论合同转让中仲裁协议对未签字人的延伸效力[J].河北法学,2009,(7):113—115.
[17]Jan H.Dalhuisen.Dalhuise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Financial and Trade Law(3th edition)[M].Hart Publishing Oxford and Portaland,Oregon 2007.
[18]张建,肖进中.国际商事合同转让仲裁条款效力刍论[J].科技资讯,2007,(15):205.
[19]Weinacht,F.Party Succession in Agreements to Arbitrate[R].Sweden Backs Down On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1999)14/9 Mealey'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port 1.
|
|
|
|
|
| 仲裁动态 |
 |
|
|
|